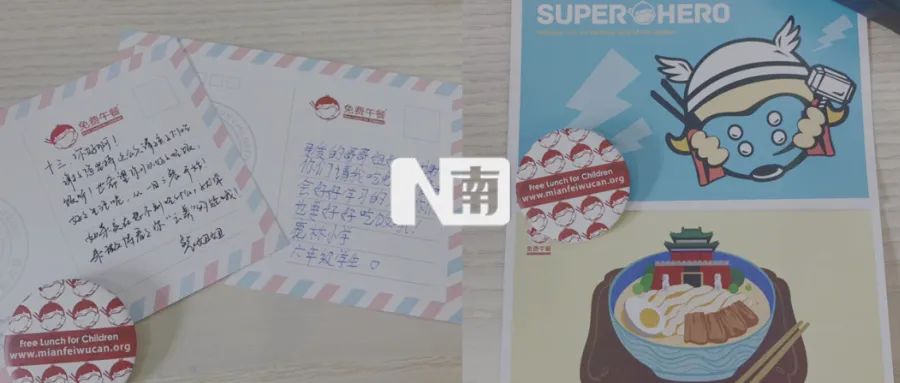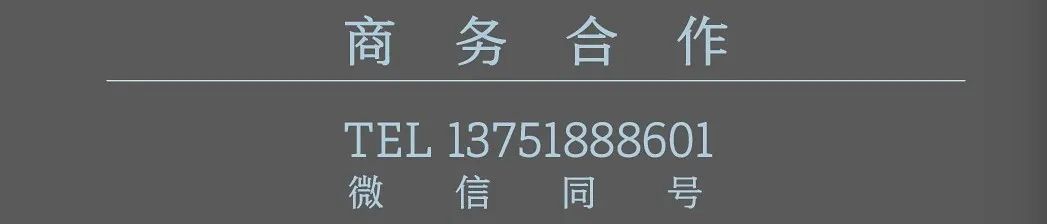在学会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之后,我们,也就长大了。
文 | 黄盼盼 编辑 | 胡雯雯
与阳光混为一色的羊群从银幕中走来,牧羊人敲打着铃铛,轻轻扬起的尘土也被阳光照亮。电影院复工首日走进电影院,我一下子就被带去了到南疆大漠的村庄,跟着艾萨迫不及待地把小羊羔从羊圈中带出来,用奶瓶耐心地给它喂奶。
小羊羔的嘴巴吃一半漏一半,艾萨一边哄一边喂,像个小妈妈一样操心。还没喂完,一个鬼灵精怪的小女孩凯丽就远远地冲过来了:“艾萨我来接小羊了!说好的各养三天,轮到我了!”艾萨着急地护着小羊:“它生病拉肚子了还没好呢,我过两天再送到你家去好吗?再给我养两天吧!”凯丽站在羊圈上,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,扮出一副女巫的腔调:“艾萨~你若是敢阻拦,我就用魔法把你变成猴子的胡子,再变成猴子的尾巴!弟弟,去把小羊抱出来!”就这样,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在艾萨与凯丽的童年友谊中拉开序幕。导演王丽娜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,先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的拍摄,再从纪录片的素材中剪辑出来这部作品。因此,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有着极强的真实感,然而又始终有一种诗意的氛围贯穿:“并不是我刻意去表现什么,而是(新疆这片)土地的光感,土地本身的氛围和生活充满诗意。”王丽娜在访谈中谈到。电影诗意而舒缓甚至支离破碎的叙事,既无法让人大笑不止,也没有让人热血沸腾,更不打算把人感动得泪流满面,总之,对于期待一场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的人,看完之后会感觉自己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。显然,《第一次的离别》并不想充当人们对电影院“久别重逢”的情绪宣泄出口,诗一般的人物对白穿插着维吾尔族民间歌谣,在光影的变化下,深入人物内心,细腻地讲述了层次丰富的“离别”故事。满屏的南疆大漠风光中,艾萨和凯丽,还有凯丽的弟弟艾力乃孜,在胡杨树下一唱一和。三个小孩身分别穿着鲜艳的红、黄、绿色衣服,无限接近三原色。仿佛一种隐喻,他们童年的底色鲜艳而单纯,情感也不掺一丝杂质。“我什么都不害怕,就害怕妈妈走丢。”艾萨是一个懂事得令人心疼的孩子,在一个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年纪,他却每天都要给母亲喂饭梳头,照顾她。他在作文中写道:“我是妈妈从外星空带来的,妈妈听不见,也不会说话,但我会用眼睛和她交流。”总是随时要从课堂上甚至从考试中被叫回去找妈妈的艾萨,和总是担心父母离婚的凯丽一样,随时都承受着失去妈妈的恐惧。两个好朋友全心全意地呵护着小羊,给小羊他们所期望得到的爱。当凯丽和弟弟抱着小羊走了之后,艾萨也匆匆跑回家,给妈妈喂饭,再把门锁好,就去追凯丽和小羊:“我送你回去,给小羊盖个房子我再回家!”在如梦如幻的夕阳下,三个小伙伴唱着跳着,阳光透过凯丽的红裙子,活泼得像一团跳动的小火苗,艾萨则在草垛上忙活着为小羊做窝。然而在开心地和小伙伴玩了之后,艾萨回家却发现妈妈又不见了。天色暗了,只能用眼神和妈妈交流的艾萨问遍了邻居,寻到无人戈壁滩上,无助地喊着妈妈。但是妈妈听不到,只剩下越来越深的夜色把艾萨笼罩。影片名字的来源是新疆教育版初一年级的一篇语文课文:“明天,我就要去县里上初中了,从此,我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分别,因此,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……”课文没有在片中出现,实际上电影并没有去刻意渲染这种离别,但离别却在影片中接踵而至。转眼间,与夕阳交界的沙漠地平线上,只剩下孤独的牧羊少年。导致凯丽与艾萨离别的,则是凯丽越来越差的普通话成绩——从35分到20分。凯丽怎么也学不好普通话,说起维语来连珠炮似的小精灵,说起普通话来却没有一个字的音在调上。在家长会上,凯丽和妈妈都被老师严厉地点名批评。虽然有人在看过电影后指出,现在的新疆不可能还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不会说普通话,但对于在维吾尔文化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来说,汉语确实是一种异质文化。“等我长大了,可以做老师,做科学家……科学家是什么?”凯丽一字一顿地读着新课文,“科学家”这个词汇对她来说过于遥远。不仅如此,平时唱起歌来眉飞色舞的她,在课堂上跟老师一起读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的时候,不仅面无表情,吐出来的普通话仿佛一个坏掉了的复读机。凯丽学汉语的难度,不亚于师资匮乏的偏远山区小学生要适应全英文教学。为了让凯丽说好普通话,凯丽妈妈决定全家搬到木库,让凯丽上语言学校去。她要离开一起长大的小伙伴,离开原来的家,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将汉语塞进脑袋,挤进汉语文化的世界,去读懂“科学家”的含义,用汉语宣誓会好好学习长大成人。在离家前夜,凯丽沉浸在离别的悲伤之中,问妈妈:“能把艾萨也带走吗?把我所有的朋友都带走,房子也带走?”而妈妈却告诉她:“不行的,每个人都要学会告别。”在妈妈的开导下,她画下了火车,艾萨,房子……所有自己不舍的东西。唯独没有和艾萨当面告别。真正的离别都发生在心里。或许当凯丽再次读起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时,就会真正读懂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,想起艾萨,想起他们一起在胡杨树下唱的歌,在相似的情感触动之下,维吾尔族文化与汉语文化终将在凯丽的情感中融合,打破她学不好汉语的桎梏,在文化的异乡之中,抵达共同的情感归宿。影片的最后,艾萨在风雪中去找走丢的小羊——那是他和凯丽共同养育的“孩子”,但怎么也找不到。这一幕和他在夜幕降临的沙漠中寻找母亲的画面,形成了一种令人心碎的呼应。风雪中的少年,最终在孤独中长大成人。成年后,世界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。在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轨迹上,很少再为任何风景驻足停留,很多人已经对离别“脱敏”。也许你我曾是艾萨,也曾是凯丽,而那只迷失的小羊,也走丢在了记忆里。编辑:胡雯雯
阅读
南都N视频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、授权联系方式
banquan@nandu.cc. 020-87006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