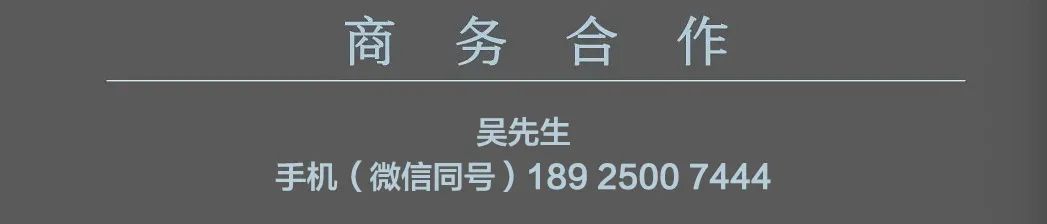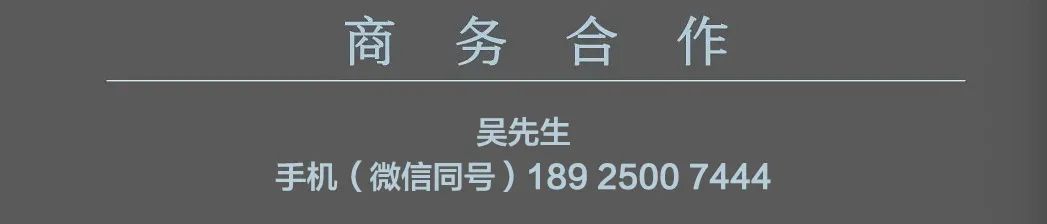这群在车水马龙的上海街道,骑着三轮车到处免费送花的年轻人,到底想干什么?一辆漆成绿色、搭配橙色自制花架的三轮车,静静停在车水马龙的上海街头,车上摆满了含苞待放的鲜花。写着大大“免费”字样的黄色标语,贴在显眼的地方。这是由活络空间设计事务所发起的“cheer up flowers-送你花”设计师行动。一位阿姨将信将疑地取了枝免费的鲜花,不可思议地感慨了一句:“这年头还有真正免费的事情啊!”这句话,让活络空间的创始人吴佳音颇有些伤感:“这年头,到底怎么了?”在她看来,在一个大都市做个免费的送花行动,是很正常的一件事,为什么如今会显得格格不入?这年头,“免费”似乎成了一个诡异的词,通常伴随着“扫码关注”或“朋友圈分享”等动作。一次次的教训,让人们开始认同,“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”。所以,当毫不掺水的“免费”来到眼前时,我们反而疑窦丛生。那么,搞一场这样的免费送你花活动,这些设计师到底在图什么?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,让吴佳音直观感受到了城市的变化:昨天还生意兴隆的店,今天可能就关了;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,就这么荒废了,堆放着物料和钢筋,像是末日大片的图景。而“社交疏远”(social distancing)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行为规范,“保持一米距离”成了一种无形的暗号。在最疫情最严峻的那两个月,任何一个咳嗽声、喷嚏声都会引起“距离”上的恐慌,“无接触”从身体蔓延到心里。春节过后,她的小区对面开了家花店,就像在“世界末日似的灰暗中点亮了一点曙光”,她赶紧过去捧回了几支朱顶红。买回来时,三四个花苞紧紧地蜷在一起,等到绽放的那刻,体积却大了将近十倍,吴佳音用镜头将其记录了下来。这种看花慢慢绽放时的治愈感,她想让更多人一起来感受。“cheer up flowers送你花”行动就这样诞生了:三轮车600元,组装的水管花架200元,再加上几天的业余时间,进行设计、组装和喷漆。一次买400枝花,价格就能压缩到八毛钱一枝。活络空间的另一位创始人王懿泉开玩笑说,这是用零花钱做一点有趣的事情。("cheer up flowers送你花行动“花车装置”)他们还写了50句中英文的祝福语,将它们做成贴纸,希望这朵花以拟人化的方式,给收花者鼓励。王懿泉觉得,她们是“在特别线上的时代,做特别线下的事情”。由于疫情的关系,大家进入了一个线上生活方式,人和人的联结在消失,对周围空间的概念也在消失。“附近的消失”这个概念的走红,来自访谈节目《十三邀》,是主持人许知远在在对话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时提出的。走在街上问路,你会发现有不少人,其实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。项飙将此形容为“当代人的一种分裂”。如果你问一个年轻人,他家周围的菜市场在哪,他很可能不知道。但若你问他QS世界大学排名、托福GRE该怎么考,这套体系他也许能讲得头头是道。对于许多人来说,自己周围的世界,似乎是一个要抛弃和离开的东西。我们默认它太俗、太无聊,如何超越周围,往往是时下年轻人更关心的问题。在项飙看来,一个人从自我层面,突然跳转到社会议题这种很大的层面,在两者间过渡的“附近”似乎消失了。“我不太信任你,但我信任支付宝。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,但我们又空前地高度信任那个抽象的意义系统。”2020年4月25日,活络空间开始了第一次“送你花行动”:在上海的老城区,从长乐路转到复兴中路。但第一枝花并不好送,还有些尴尬。刚开始,参与的志愿者骑手们没有太多经验,也没有解释这次行动的由来,只是直接递花给路人:“你好,我们这免费送的”。大部分人忙不迭地摆手“不要不要”,也不敢接花。有些被花车吸引的人,也只敢站在一二米开外的地方,好奇地盯着,一旦骑手们上前告诉他们免费送花,得到的也是“不要不要”。人们对于“免费”,似乎已经产生了本能的警惕。那种抗拒感,吴佳音形容“就像抗拒街上给你发传单的人”。正如项飙所说:过去我们有自信在自己“附近”构建出一个爱的关系,但现在,我们好像丧失这种能力了。每一次收快递、拿外卖,大都是和一个陌生人的临时性互动。而“送你花行动”,却是另一种偶发,构建起的社会关系更加微妙。车骑到常熟路附近时,一位中年男士腼腆地问,能不能拿一枝花?爱心骑手顺着男士的方向看去,发现有位女士抱着膝盖,闷闷不乐地坐着,看上去俩人似乎刚吵过架。女士没有抬头,而男士拿着花,想给又不知道怎么给,有些不知所措。于是,骑手们一起走上前:“阿姨,这花是我们免费送的,希望你能开心。”“这种偶发性的感觉挺奇妙的,如果没有遇到这辆花车,不知道他们沟通的转折点会在哪里,他还会想什么办法给女士道歉?”吴佳音事后回忆。还有一对被花车吸引的外籍情侣,男生了解活动内容后,很开心地拿了一朵大红色郁金香,直接在路上单膝跪地,将它送给了女友。另一对收到花的情侣,则当着大家的面,隔着口罩亲吻了一下。其实这也就是“送你花”的初衷:通过实践一个善意的行动,牵引出美好的结果。迄今为止,她们已经在上海进行了5次行动,每次都会招募爱心骑士参加。“我终于找到你们了!”不少人是看到了骑手的朋友圈后慕名过来,在街头等待这个偶遇的。在茂名路附近时,一位小区保安也加入了行动中:“他们真的是送花的,他们真的是在做善事!”这位保安热情地吆喝着,还拿出有孙子照片的定制手机壳,与大家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最后,保安收了一支鲜艳的郁金香,开心地志愿者们合影。2020年 9月“设计中国北京”展会期间,活络空间带着“送你花行动”到了北京,还入围了2020北京设计博览会“月桂奖”最具公益影响力奖项。(2020北京设计博览会“月桂奖”最具公益影响力奖项,左二吴佳音)
在期间的“创造治愈设计师对谈”论坛结束后,一个小姑娘特地来到活络的花车旁,请求与吴佳音合影,“听论坛的时候我都哭了,知道还有人在做这种公益性的、纯奉献性的事情,真的非常感动。”而在这次行动中,吴佳音也产生了一些有趣而严肃的思考。比如,她们从没想过,在上海街头骑三轮车是会被盘问的。每到一个新的路段,她们都会遭遇询问情况的市容人员,得知活络空间是在免费送花而非营业后,市容工作人员则会远远地跟着,查看情况。“在我看来,骑三轮车就像骑多个轮子的自行车一样,应该没什么特殊的呀。”但询问了有关部门三轮车的行驶规范后,她们得到的答案却不尽相同。上海市公安局交通部门网站的信息显示:自2017年1月1日起,未领取“2016式”非营业或营业人力三轮车牌证的公车和私车,禁止上道路行驶,违反规定的按照有关法规处罚。王懿泉在街上询问过交警,对方说只要不给三轮车加装改装电动马达,就能正常上路。但不少街口的交通标识显示,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可以骑行,其他时段则不允许三轮车骑行。她还记得,小时候的北京街头随处可见三轮车:五金店的、早餐摊的、蔬菜水果店的流动摊贩们,还有送孙子孙女上学的爷爷奶奶……而自己十年前大学搬宿舍时,也是骑着从食堂借来的一辆破旧三轮车,一个人搞定的,“当时感觉自己还蛮酷的”。而现在,三轮车似乎跟着许多东西一起消失了。越来越密的都市丛林,城市化的快速进程,人口的大量流动,让人们的生活也互联网化,社群变成了一个个社交平台,社会环境就是整个网络世界,每个人都量化为一堆数据:年龄、消费能力、每年出行次数、浏览习惯、粉丝数量等……在吴佳音看来,这种环境中是很难建立真正的沟通和信任的。她期待在未来,将“cheer up flowers送你花行动”带去更多城市。活络空间还打算记录下每次送花行动中的点滴,将这些足迹做成一本出版物,甚至办一次回顾展,让这些故事唤起更多人对于公共空间的思考。“也许这么几次小小的送花行动太微观了。但是我觉得,在我们送出每一枝花,并且得到市民的理解和采纳的每一个瞬间,是有一点点撬动了信任基础的。那一瞬间,我们与领花人之间的信任隔阂是最小的。我想,对于这个行动来说,有这些瞬间,就够了。”
编辑:胡雯雯

南都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授权联系方式
banquan@nandu.cc. 020-87006626